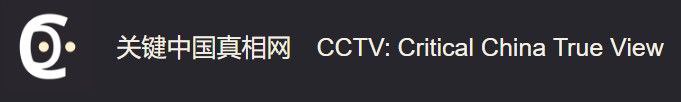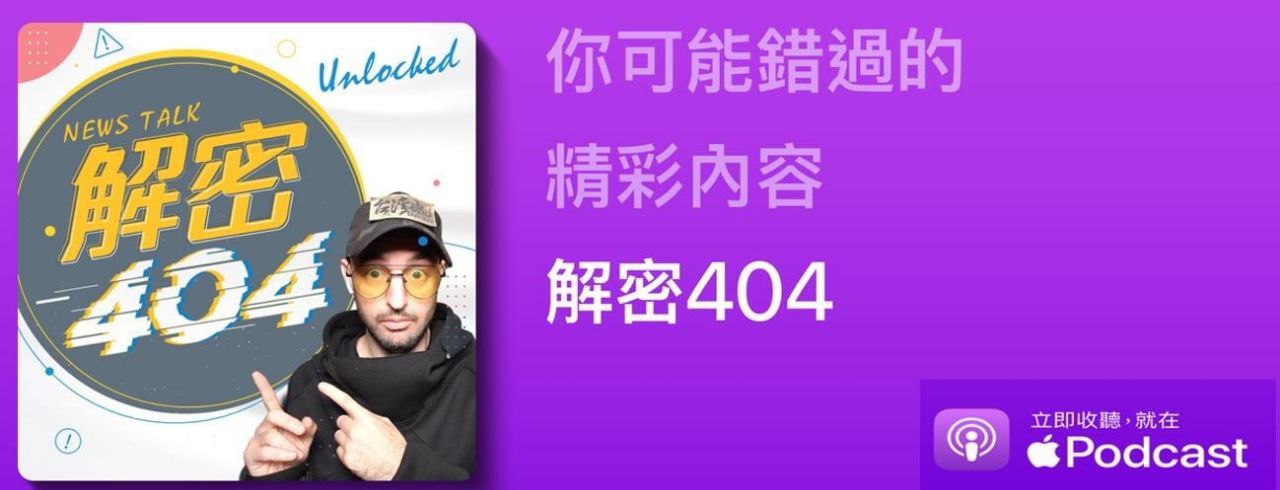【2025年10月16日訊】(記者方曉綜合報導)中國大陸社會對「剩男」「剩女」的話題始終熱議不絕。然而,這兩個現象的背後,並非僅是個體選擇或「眼光高」所能解釋。人口學家指出的,「剩女」只是浮於表面的假相,而由中共非人性化政策製造出的「剩男」危機,才是深層的社會真相。這場席捲全國的婚姻危機,實質上是中共長期實施的戶籍制度與計劃生育政策,在人口結構與社會倫理層面引發的雙重崩塌。
財經大V「平說財經」10月16日撰文表示,僅上海一地就有超過200萬女性不結婚。業內人士認為,這些女性多半「眼光高」,希望找到條件更優的本地男性;但本地優質男性數量有限,最終導致她們選擇單身。
事實上,這類女性普遍具有高學歷、穩定收入與獨立人格。她們的存在並非上海獨有,北京、深圳、廣州等大城市亦呈現相同趨勢。
「剩女」一詞最早來源於2006年《時尚Cosmo》雜誌的一期封面。意為已過適婚年齡,但是仍然未結婚的女性。
2007年後,這一詞條就被收入中共教育部發布的《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的漢語新詞之列,並定義為:高學歷、高收入、 27歲以上仍然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歸宿的女性。
中國到底有多少「剩女」?
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曾引用某婚戀網站保守估計,全國剩女已近一億人。剩女有很多,一線城市的剩女更多。
根據2025年上海市婦聯的調查,未婚女性已突破200萬人,較2015年增長70%。其中,25至34歲女性中有40%處於單身狀態。
上海「剩女」現象的深層結構性成因
對於上海「剩女」現象,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的報導承認,表面上,「眼光高」似乎是上海「剩女」的主要原因,實際上,這只是戶籍制度壓力、資源錯配,以及婚姻市場失衡的反射。
報導說,在 戶籍制度的政策壁壘方面,中共的戶籍制度將醫療、教育、養老等核心資源與「本地身分」嚴密綁定。對女性而言,尋找本地戶口的伴侶,實際上是為了確保下一代能獲得基本社會保障的一種理性防禦,而非勢利之舉。
在資源錯配與婚姻市場失衡方面,優秀的外地男性,儘管收入高、學歷好,卻因缺乏政策賦予的城市資源,被排除在婚姻市場之外。這使得滿足「本地+優質」條件的男性極度稀缺,從而導致大量女性「被剩下」。
新一代女性的價值觀變化
上海靜安區社區服務中心的一次小型訪談中,30歲的設計師張悅道出了許多年輕女性的心聲。她坦言,母親一輩的婚姻生活讓她對傳統角色分工產生質疑。「我媽每天操持家務,父親卻鮮少參與,這種模式我不想複製。」這種觀念在90後、00後女性中頗具代表性。
對她們而言,婚姻不再是生存的必需,而是平等與精神契合的選擇。經濟獨立讓女性對婚姻的期待更高,渴望真正的互助與尊重。
上海某婚戀平台2025年調查顯示,62%的男性願意與妻子共同分擔家務,較2015年上升38個百分點,顯示家庭性別分工正在發生變化。
「剩男」真相:計劃生育的社會惡果
相比於城市「剩女」的主動選擇與高要求,「剩男」問題才是中共社會工程政策造成的不可逆轉的災難性後果。
「剩男」是指超過適婚年齡(通常30歲以上)仍未婚的男性群體。
中共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實施限制人口出生和「獨生子女」的「基本國策」。導致了大量選擇胎兒性別的非法墮胎。在大陸農村地區,有人為了確保生男孩,所以做B超鑑別胎兒性別,是女孩就墮胎。
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中國的性別比例嚴重失衡。1980至2010年間,中國男性比女性多出約3,600萬人。
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國出生人口性別比達118:100,遠高於正常值。80後非婚人口的男女比例為136:100,70後更高達206:100,且年齡越大,失衡越嚴重。
人口學家李建新指出,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出生性別比長期高於115甚至120,遠遠偏離自然值,導致婚姻市場極度失衡。
結構性崩塌與國家級危機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帕斯頓教授早在2020年前就警告,中國將有4,500萬至5,000萬名男子終生無法找到配偶。
「女權無疆界」創始人瑞潔(Reggie Littlejohn)亦指出,罪魁禍首正是中共推行三十年的獨生子女政策。這一政策導致至少3,700萬女性「被消失」,嚴重破壞人口自然平衡。
「男多女少」的社會給人口再生產帶來嚴重障礙,造成人口嚴重萎縮。因為人口的再生產主要是通過母親來實現的。女性在社會人口中比例的萎縮,必然會導致人口再生產能力的降低。
聯合國預測若生育率長期低於1.5,百年後中國人口將降至5億人,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將超過40%。
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博士梁建章指出,中國如此劇烈地改變人口結構,「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足以成為全球人口學的警示案例。
人為政策扭曲的人口悲劇
「剩女」與「剩男」表面上似乎是個體選擇的結果,實則是制度性壓迫與人口工程的副產品。前者折射出女性追求平等與尊嚴的覺醒,後者則揭示了計劃生育導致的社會性別災難。無論城市女性的孤獨堅持,還是底層男性的無力掙扎,最終都指向同一個事實——中共長期以來對人性與自由的壓制,正讓這個社會的人口結構走向崩潰。
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