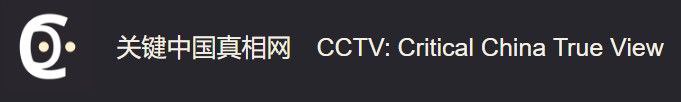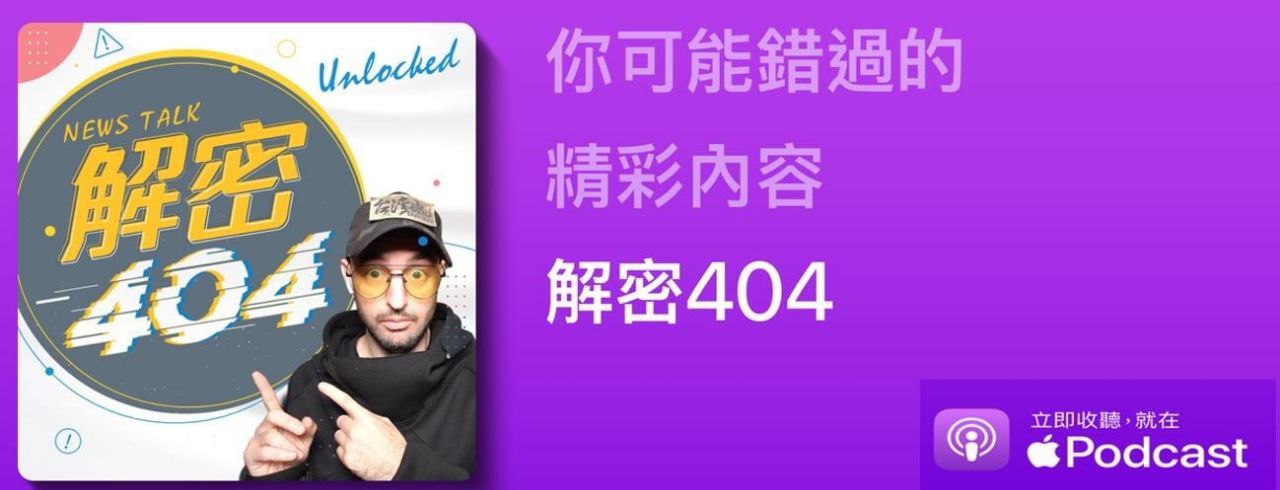香港电影曾是华语世界最耀眼的文化象征,从王家卫长镜头下的浓绿与霓虹,到杜琪峯冷峻镜头下的兄弟情谊;从梁朝伟用眼神切换角色的情绪,到张国荣只用肢体语言成就永远的阿飞;从周星驰对喜剧演绎的重新定义,到许鞍华对小人物的深情凝视—这些影像不只是娱乐,更是一整代人的集体记忆,以及香港人的文化遗绪。
那是个港片创作者可以大鸣大放的年代,是香港电影公司与导演能把脑中世界在银幕上肆意绽放的黄金时期。然而在中共治理的牢笼下,这一切已沦为只能在怀旧中追忆的文化遗骸。
审查机器下的集体失语
香港电影在港府修订《电影检查条例》后,送审的近4万部影片中,因「维护国家安全」被迫修改内容的共有50部。另有13部不获核准上映,至今仍无法得知是哪些电影被消失。这些数字背后,更多电影可能在剧本尚未完成时就已开始受到禁锢,创作者在自我审查中阉割掉所有可能触碰红线的灵魂,本土故事被中共式主旋律逻辑淹没。这种审查不单只是体现于内容的审视,这种审查是如浓雾蔓延在中国想控制的每一份土地上,中共让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的《1984》的世界展现于世人眼前。
令人讽刺的是,中国蓬勃的网络城墙内,有众多对于港片相当推崇的人。时常把经典作品拿来做研究、写文章分析并剪辑影片做解说来缅怀,常常感叹港片过去的辉煌与现在作品不如以往。
但在不自由的过度里去怀念曾经创意既没有地板也没有天花板的电影文化,只不过是在纪念一具被强制抽干灵魂的精致躯壳,那股可以在东亚文化圈独树一格的创造力正是被威权体制下进行系统性的扼杀。中国网民的感叹多了几分平庸的邪恶的即视感。
平心而论,香港电影的衰败当然并非单一因素,盗版横行加上香港面对九七回归让许多人选择移民让电影人才流失,加上当时许多名导与演员都相继转向挑战好莱坞,这些因素都在九零年代后对港片产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尤其是黄金世代的影星后面并没有同等影响力的接班明星出现,至今我们仍可以看到许多年近六七十港星们还在散发他们的余光去成为现在中国与香港电影里面的亮点。
但要说港片在进入千禧年后就一路一厥不振到现在吗?其实如银河映像出品的一系列佳作、市井电影、王家卫的文艺电影以及不得不提的无间道系列都持续为香港注入港片灵魂。
随着中共对香港进行政治的紧缩与管制高压下,香港电影也逃不过全面审查的命运,导演的创意与领感需要被审查、演员要爱国加上因为资金问题让许多港片都是中港合拍,更不用说成片后又要面临意识形态审核与删减。很多人将《无间道》系列形容是香港电影最后的余晖,其实不然,或许它是重新开启另一个不同于过去黄金时期的新开端,只是被中国一步一步地踩熄它本应重燃的光辉。
或许你会说近期院在线还是有许多大制作的港片问世,许多影片光看预告片就很吸引人。如《金手指》、《风林火山》等作品集结了如金城武、梁朝伟、刘德华、刘青云以及古天乐等港片象征,更不用视觉特效上每每都在进行突破。如同上面提到的,这些港星通常都会是电影的亮点,这些电影阵容可期但剧情在审查的红线下变得谨小慎微,通常预告片都会比正片好看,内容已经少了过往港片独有的生猛感与市井气息。
这些披着港片外衣的中资电影,更多时候只是在消费过往港星的形象,将他们变成象征性的符号,观众看到的是熟悉的面孔,电影里做着过往他们的招牌动作。但再多滤镜加持就顶多只是卖出一份怀旧感。

中国电影的相同宿命
这种对电影文化的破坏并非香港独有,毕竟中共是非常著名的文化破坏集团。曾几何时,中国电影也有过极具批判性与创造力的黄金时代,如进入八零年代后,不乏有《大学生轶事》、《黑炮事件》、《活着》、《霸王别姬》等作品,敢于面对历史创伤、嘲讽官僚主义、接露社会矛盾与体制的不公。
中国电影也随着国力的增强,在城市高速发展中产阶级数量提升有了把电影作为休闲娱乐的市场下,电影也进入了高成本的大制作时代。《英雄》、《夜宴》、《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大作虽有商业妥协以及中国在电影展现国力的影子存在,但仍保有创作者的美学追求。期间也许多在大导演大制作底下仍难以忽视的社会写实电影与独立电影受人推崇,如宁浩导演的现实性喜剧、贾樟柯视角下的大国角落的小人物还有许多带有纪录片色彩的文艺电影。
在习近平上台后也难逃电影产业受到意识形态强烈控管的命运,随着2016年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中国电影制作到上映要通过层层关卡,任何人都没有一套可以通过审查的表准,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电影变成需要姓党、听党、爱国的行业。
时至今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电影院里充斥着主旋律电影。《战狼》与《长津湖》系列都能占据中国影史票房排名前十以内,如《八佰》、《东极岛》、《南京照相馆》等抗日爱国题材更是持续地将中国民众困在狭隘且偏激的民族叙事中。
中国电影产业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要做出同时兼具创作、市场以及审查的电影比登天还难。更不用说中国民众也会协助中央对所有的电影进行没有标准的思想审查,爱国与叛国都可能在一些没有意义的画面与字句之中。

无一人能幸免,从张艺谋、陈凯歌、贾樟柯到后起青年导演,都必须在体制框架内「讲好中国故事」,艺术表达与反思精神被压缩到几近于无。
牢笼下的香港电影
从《国安法》到《电影检查条例》修法,再到基本法23条立法,表面上是对香港体制的强制控管,以及对「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彻底失信。但实质上,中共已经对香港进行了一场文化改造。
如今,我们只能从电影与饮食中回味记忆里的香港文化。审查的不只是电影,而是所有的思想与言论。港府对所有电影的严查就足以证明任何要进入香港或出产的电影都必须经过不透明的审查流程,就连创作者过往的言行都必须被检视。
香港电影在这种压抑的体制下,与中国主旋律当道的票房市场不同,近几年打破港片本土纪录的两部电影《毒舌大状》与《破·地狱》都不是大制作、大明星阵容的产物。这也体现出港人透过观影选择来倾吐自己心声。
两部都由黄子华主演的电影,前者是小人物对抗只手遮天的强大势力无奈、奋力挣扎再到最后排除万难在法庭中求得「公义」,后者从殡仪业视角看到香港传统文化与社会的缩影,并描述亲情问题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
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引起共鸣,正因为它们某些层面婉转的触及了香港人当下的真实处境。透过电影感受到失去公平正义后能被讨回来的快感;被电影「破」除执念与创伤完成属于活人的渡化。
但问题是香港人真的有机会「破」地狱以及找回自己的「公义」吗?在日益紧缩的审查环境下,这样的作品未来还能保有空间吗?或许这就是香港电影目前必须接受的处境。
华语电影是多元汇流而不是单一文化
文化是经年累月透过历史去炼造出来的产物,电影就是其中一个呈现方式。如同李安导演曾说「格局」是一种文化涵养。它就不是一个可以跳过所有脉络去囊括一切的物品,如同时常有所谓「去中化」的批评出现,但批评者有理解何谓「中华文化」吗?
而这文化该由谁定义?各国的华语电影就是有别于中共文化与民族叙述的产物,电影是电影,但中国就是中国,华语电影本来就不只属于中国。
台湾电影也是华语电影文化的一角,一直以艺术性高、强烈导演风格且写实闻名,过去有重美学轻产业这种较不具娱乐的特性。在电影产业中是独树一格的存在,常常是享誉国际,不过叫好不叫座。但随着近年新锐导演的崛起,台湾电影也逐渐透过多元视角与议题渐渐在影片呈现上既能抓住民众眼光也能得到国际赞赏。
从台湾到香港的电影文化发展来看,华语电影在不同地域的呈现本就该是多元的。电影作为文化载体,必然反映出该地的社会脉络与文化特质,这是由下而上、长时间累积而成的结果。
当我们将视角转向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更能看见这种多元性的丰富面貌。这些地区出产的华语电影带有浓厚的文化融合色彩,从《爸妈不在家》、《南巫》、《富都青年》到《男儿王》等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当地独特的文化肌理与叙事语言。
而金马奖的意义,正在于它作为一个平台,让这些来自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的华语电影得以汇流交织,彰显华语电影世界的丰富与多样性。
金马自由奔腾
金马奖迈入62届,除了持续作为华语电影奖最具影响力的标竿以外,它仍是包容性的象征。有人缅怀过去两岸三地明星云集的盛况,感叹如今许多大咖影星都不来参加。
但必须厘清的是禁止影视人员来台参与金马的一直都是对岸,台湾从未设下任何限制,透过电影交流的大门始终敞开。相较于中国官方色彩浓厚的金鸡奖,金马奖对所有华语电影敞开大门。
这正是为什么金马奖能成为华语电影界最具公信力的奖项,它代表的不只是专业肯定,更是对创作自由的尊重。金马奖不论过去到现在,都是培育与肯定杰出华语电影工作者的摇篮,而非一场只能接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商业秀场。
至今仍有许多香港演员与导演在努力,他们或许无法在香港畅所欲言,但在金马奖上他们的声音仍有回响的空间,在台湾它们可以不背弃理念的展现创作。香港仍有导演产出属于自己的都市节奏与本土关怀。而台湾最重要的价值,是成为让华语电影创作者能在没有禁锢的土地上自由表达的地方。
当香港、中国的创作空间日益紧缩,台湾必须守住这片自由的土壤,让华语电影的火种不至于熄灭。当我们缅怀那些经典时,我们缅怀的其实是一个创作者能够诚实面对现实、大胆表达自我的时代。
那个时代在香港或许已经结束了,但属于新世代的香港电影或许正在重新萌芽中。只要还有自由的土地存在,属于华语电影的文化与精神就不会真正逝去。